由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云中漫道”学术讲堂第十五期“黑格尔与现代国家”于2020年6月10日18:30-20:30,依托腾讯会议平台以线上方式顺利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作为主讲嘉宾,由马克思主义学院陆永胜教授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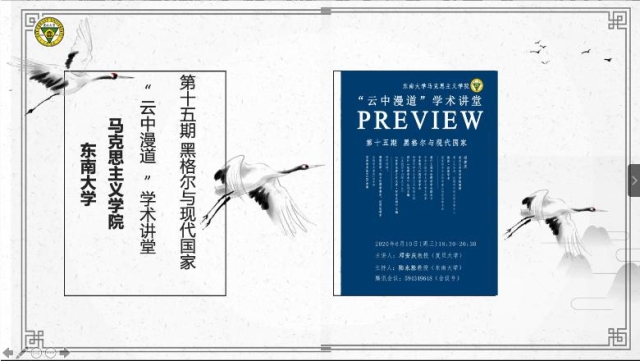
本次讲座主要围绕黑格尔国家理念的现代性这一问题展开。首先,邓教授指出,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黑格尔的国家理念至今受到的误解最多,尤其是国内学术界,许多人依然把黑格尔视为一个“专制国家主义者”的代表。邓教授梳理了黑格尔去世以后,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其国家学说进行批判的两条基本线索,认为马克思的国家观念与黑格尔的国家观念确实存在着较大分歧:马克思对国家充满着不信任,认为国家最终是要消亡的,在其消亡之前只是作为阶级斗争的暴力工具存在;而黑格尔把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自由规范秩序的最终实现,他从历史的视野将现代国家理念返回到柏拉图时代的城邦国家理念,寻求其合理性的源头,这就是正义。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探讨作为伦理理念的正义如何在城邦国家中实现的学说。但柏拉图正义理念的最大问题,在于他的政治哲学无法安顿已经出现的个人自由意识和城邦理念之间的冲突,因为个体及其自由的观念在古希腊还得不到承认。现代伦理已经以自由为基础,个人自由通过罗马法的私人财产权和基督教的教化而成为了现代人的自觉意识,而个体自由权力如何与来源于柏拉图的城邦正义相结合,便是黑格尔国家理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接下来,邓教授通过引用哈贝马斯的话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哲学家,他开启了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但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使其思想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由此开启了对黑格尔国家观念的批判。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思想看作是保守的、官方的、专制主义国家理念的代表,这种观念到现在一直根深蒂固。而邓教授试图从黑格尔国家观念的“古今之辩”来为其“现代性”辩护,其“保守”的是“国家”实体中内在蕴含的理性力量与正义力量,通过国家的“伦理性”来超越英法激进自由的国家观念的根本缺陷。
邓教授在简单介绍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评之后,重点讲述了现代自由主义者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评,认为以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为标志,从黑格尔1831年逝世后到1945年近100年来,对黑格尔国家观的负面评价在这里达到了高峰。在邓教授看来,波普尔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与事实不符、因而存在严重问题的:首先,从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来看,黑格尔在学生时代就热烈欢呼法国大革命,他对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的变化从他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可以看到,但他从来没有否认而是一直坚持自由的价值;其次,黑格尔并不是由复辟的反动派、相反是由改革派大臣引进到柏林大学的。因此,黑格尔去柏林不像波普尔说的那样是满足反动派反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性能需要而“受命”的,黑格尔自己在“柏林大学开讲词”中对现代国家的精神和哲学的时代使命的意识,以及他在柏林大学心目中的形象,都是一种进步的、自由的“精神领袖”形象。
邓教授特别指出,二战之后西方经历了一个黑格尔主义复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黑格尔正面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在为黑格尔国家观平反过程中,伊尔廷(Heinz Ilting)编辑、注释和评论的《黑格尔法哲学讲演录,1818-1831》四大卷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伊尔廷教授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有1820年的流传版本和黑格尔讲演录的“秘传版本”,通过这些版本的对照,人们不难看出,流传的法哲学版本是由于《卡尔斯巴登法令》颁布后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的影响而出版的,文字上表面的对国家的颂词只不过是严峻政治形势下的一种修辞,而不能因此而否定黑格尔国家观念的现代性。邓教授通过具体解读黑格尔法哲学第258节“补充”部分广受诟病的国家观,阐明了该如何正确理解这一节的合理内容问题。
邓安庆教授认为,黑格尔强调国家是一个理性的有机体,是伦理理念(自由与正义)的实现,核心是阐明一种自由的规范秩序所需要的各种社会的、精神的、历史的、道德的和伦理的、乃至世界历史的条件,国家本身作为客观精神并非是最高的,其使命还需进入世界历史进程,接受世界历史这个“法庭”的检视。国家的现代性,核心的是处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自由主义最小化国家的方案,在黑格尔这里受到了抵制,黑格尔指出了如果没有一个以现代伦理理念为使命的国家,市民社会一个以需要的满足、特殊性充分发展为目标,最终会导致其自身无法解决的恶的无限性,导致对社会自由的否定。国家最终实际上是社会的自由而正义秩序的完成,而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专政机关。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最终都将在国家的规范秩序中获得充分而完满的实现。黑格尔与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市民社会内在局限究竟最终是由社会自身解决还是只能在国家层面解决的分歧。
最后,邓教授的结论是,黑格尔的国家不是专制国家,他强调国家法治,一切法宪的目的是自由。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是国家稳定和强大的基础,国家不取消而是保障自由的实现。个人自由权利的实现既是社会也是国家的使命。他的国家也区别于罗马帝国,因为他把政治的公共性确立为自由相生的领域,以法治制度防范任何一种把公共权力变成私有财产的企图;他的国家也区别于中世纪的神权国家,强调教会与国家的严格分离,将宗教划归私人生活领域,将国家保持为公共政治领域。

在提问交流环节,邓安庆教授与同学们进行了线上学术交流互动。同学们积极发问,从对“恶的无限性”的理解,到如何看待马克思与黑格尔国家观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再到关于“自由优先与正义,正义优先于善”问题的看法,邓教授一一做出了解答,同学们纷纷表示这次线上讲座拓宽了视野,令他们受益匪浅,收获良多。
邓安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伦理学学科点学术带头人,德国洪堡学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上海市伦理学学会副会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轮值主席,担任《伦理学术》丛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哲学、西方伦理学通史、应用伦理学,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供稿人:费晓宇、田怡;审稿:翁寒冰
